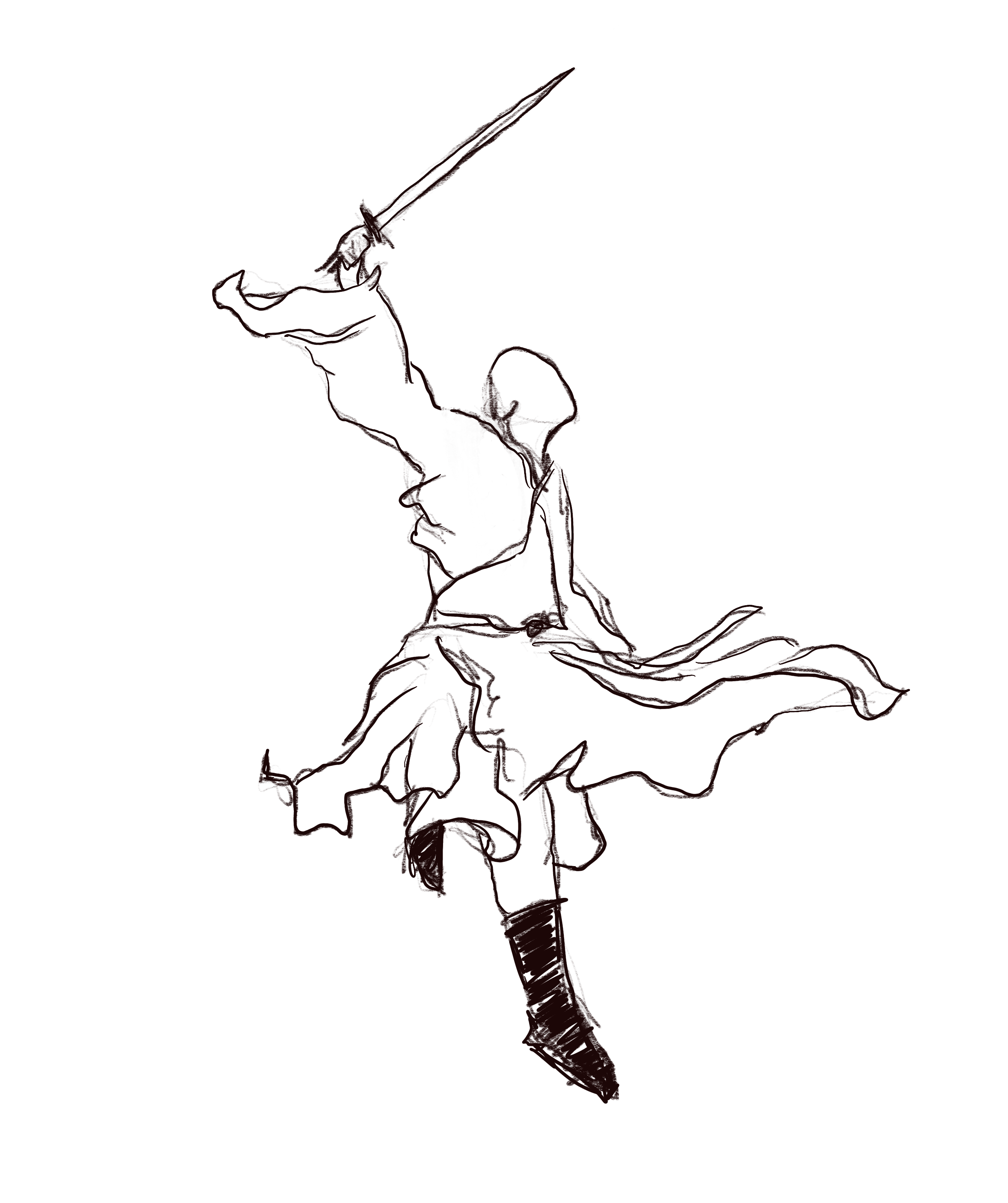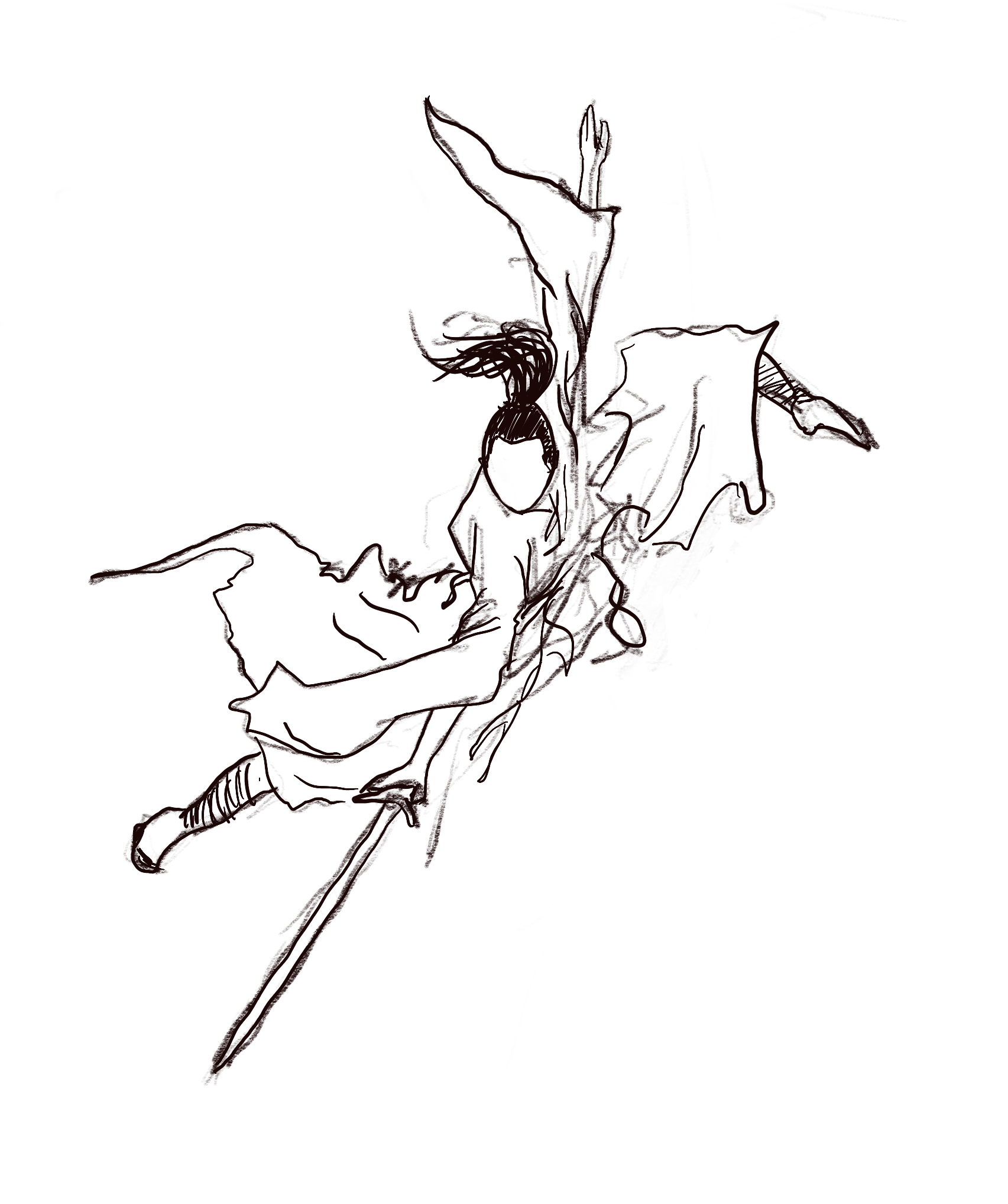25年夏日的一些杂想
女伤春,士悲秋。我认为每年的夏至日最为悲伤,因为这是一年间日照时长逐渐变短的起始。
我想记下一些自己的Summertime Sadness,无论是作为激励还是回忆。
一些追忆
昨晚与朋友闲谈计算年龄,忽而惊觉自己已然二十有三,我想是生日刚过不久还未从上一岁的印象中走出的缘故。我仍清晰记得17岁那年生日与同学在外地集训,零点之际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发出一条多愁善感的空间动态:
17岁了。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想哭。
彼时每增长的一岁都是那么地真真切切,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同时又伤感自己不再年轻、不甘于未能取得所期望的成就。可笑的是,这种对年华流逝的敏感似乎在过了20岁后便不再那般强烈,仿佛奔三的过程已然让我麻木,将这十年视作了一个目睹希望逐渐流失的整体,不愿将它的伤痛以年为单位去逐一经历。
我仍记得20年疫情的那个寒假,我的心中没有对即将到来的高考的惶恐,亦无心为之做出太多超越自己实力的努力,只是一心幻想着到了大学后甩掉众多学科的束缚专攻于一门技术的畅快。我在知乎上为百天之后的高考留言“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在“一句话形容数学”的问题里留下”Mental Abuse To Humans, My Approach To Happiness”的回答。我以自己可笑的数学水平在知乎的数学专栏文章之间流连,暗想自己今后也能在某一领域写出这般底气十足的文字。我研究着各类古怪的数学问题,与好友交流;不知多少个下午就在盯着草稿纸发呆中轻飘飘地度过。我也满怀志向地开启自己的专栏,零零碎碎的三两篇文章记录着凑巧解决的数学题,有圆锥曲线的,有组合数学的,也有从3B1B上看到的概率问题。20年的三月与同学一同参加了阿里的数学竞赛,还记得线上的比赛有多日的作答时间,而我在一天晚上睡觉前想出了一道组合题的做法,激动地爬起来以高中生的简陋数学语言洋洋洒洒写满一大片步骤(此题最后确是满分,怀疑是阅卷者懒得细看的缘故)。之后与我一起参加的同学入围了决赛,而我猛然发现自己离分数线也不过一题,顿时又对自己的水平有种飘飘然的自信…
本科报道那天,我抱着一摞书进宿舍,我记得一位新同学以诧异的眼光盯着我手中的书,挑起一本《初等数论》草草翻了一翻,吐了吐舌头走出了我的房间,是啊,我当时也以为自己会在四年间细读这本书呢。可是第一学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化学、英语写作、英语口语,却让我痛苦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原来到了大学,我依旧不能只学自己想学的。我于是与同学们一起,为了绩点和作业挣扎,期间我也试着以不同的方式记录着自己的足迹,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大一大二时用的是github repo,大三自学操作系统时则重回知乎写起了专栏,之后又转而开启自己的博客网站。然而不论是哪一次踌躇满志地开始,最终都得到一个空有外表的结果。我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平庸的真相,不再为听不懂数值分析的课程而苦恼,翘课就行眼不见心不烦。遇到不擅长的ECE课程时,我不再逼迫自己全盘听懂,只指望着依靠考前的突击去记下一些解题的公式,熬过一个学期就行,我因此获得了更多自由的时间以挥霍,也付出了专业水平空空如也摇摇欲坠的惨痛代价。大三时,我时不时有一种想法:似乎所有我学过的计算机知识都只在脑中驻留了片刻便被忘却,真正留下的一些朴素的理解其实一夜之间便可罗列完,相当于我三年所学完完全全可以被旁人以一晚上时间企及。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不寒而栗。我的一无所成也伴随着大三暑研的结束而到达了巅峰,回想那个暑假我所见过的人和说过的话,我想我彻底正视自己本科的失败便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大四一年过得既快又慢,我第一次真真正正认识了一帮称兄道弟的朋友,仿佛头一回完成了大学第一个学期应该做到的事情。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因为我们几乎每两个人之间都以不同的原因有过一种bonding,或是课程组队,或是宿舍同区,或是爱好相同,而两两间的化学反应又在一整个小团体内显得无比和谐,没有人会担心自己的话“掉在地上”。我们时常三三两两相约自习、运动,隔三差五出学校吃饭、喝酒、唱歌。可以说,我在大四才过上了别人口中的“大学生活”,也是蛮奇妙的。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认识的这些朋友,以及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一些朋友,是我本科四年唯一可以宽慰自己的收获了。而除了享受生活外,我的大四一年不过是“混吃等死”罢了。记得最痛苦的时刻在于写硕士申请的Statement of Purpose之时,我盯着自己寥寥无几的简历苦笑,不得不直面自己大学四年一事无成的事实。讽刺的是,我曾以为那将是我最后一回humiliate myself,谁曾想在现如今的几个月后我又将有幸重温那样的痛苦,只道是造化弄人吧。大四一年我的课程基本是虚度,以至于身为Computer Engineering专业的学生却很不幸地落下了对嵌入式系统几乎一无所知的病根,甚至毕设的小组展示我也是在截止日期前一夜奇迹般地做成,足见我当时对学业和人生的态度为何。
一些近况
我的硕士生涯很短,如今已然过半。不幸的是即便身处自己的“主场”UIUC,我依旧没有对硕士的生涯做出合理的规划。我稀里糊涂地选着课程,以至于两个学期所学的与科研所做的之间不能说南辕北辙,只能说毫无联系。现在想来这着实非常讽刺,因为我已然度过了本科前几年间没有选择权的无助,却没能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自由。
回顾一年以来浑浑噩噩所混过的课程,所幸倒有一门令我感叹“不虚此行”。这门课的教授已然75岁高龄,他会于周末以电邮向学生发送两份下周的课件,于上课时传递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让到课的学生签到(我常常与同学打趣,为这位德高望重的大牛签名十余次或许是我学术生涯最大的高光了)。在第一节课过后,教室里所剩的学生便不到十人了,这个数字在几周后很快固定为了“9”,学生的稀少导致大家不久便相互脸熟,教授其实也不再需要传笔记本签到,因为几乎无人缺席。 课程的名称是Concurrent Programming Languages,其内容则基本为纯理论的Computer Science。我在第一节课就眼睁睁目睹教授随随便便地向大家抛出了满是数学定义的Latex,其中的Category, Group仿佛死去的回忆向我袭来,倒不是我曾经学会过,只是突然想起了20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暑假。我于是极尽全力听完了他的第一课的思路,并毅然决然地踏入了这深不见底的数学深渊。而后的一整个学期,我所听懂的内容约莫有50%,却已经是燃尽了自己所有可悲的脑力。所幸这门课并无作业或考试,只有要求学生轮流上台在课程结尾回顾上周的内容(以及期末完成一课程项目),每每轮到我时,我都汗流浃背,不得不提前几日将课件翻来覆去抄了又抄,依然逃不过于台上被问懵的结局。教授的脾气极好,即便是对我这样满口无言乱语牛头不对马嘴的学生,也以同辈学者之间的态度平等友好地交流,仿佛我对数学概念胡乱模糊的描述都是无伤大雅的口误。受他的影响,我在上学期助教CS 101这门课时,面对满口胡言的学生,每每心生厌烦时总是在脑海中浮想起自己在教授面前的狼狈,遂也不自觉地模仿起教授的态度对学生们笑脸相迎。教授时常在课堂上鼓励大家提问,他不止一次非常认真地向我们强调,这几十分钟的内容不是面向全世界,而是专门献给在座各位的,假如不当场将心中疑虑提出,就没有意义了。此外,教授也经常敏锐地注意到台下抓耳挠腮的我,并温和地伸出手指道, “you’ve got a question.”
该课程中最令我触动的一件事,发生在一次课后。记得当时我全程听得云里雾里,只好抓着中途丢掉思路的位置胡乱问教授一个证明,结果教授三言两语便用课件后部的内容将其解释了,并满怀期待地看着我问是否明白(我自然是苦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我向教授诉苦自己对于他上课所频繁提及的代数概念实际上一知半解,以至于对重要概念的理解应该有不少偏颇。闻言教授非常严肃地拉着我坐下,连同陪我的同学一起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两点:一为探讨为什么我的代数基础不行,二为analytical thinking和终身学习的意义。教授以学习中文作比,他这么多年与无数中国人合作科研,可是他没有认真去学依然听不懂中文,而我作为计算机工程本科出身,没有耳濡目染代数的基础也是可以理解。同时他强调”the math you learned in undergraduate is insufficient, you guys were CHEATED”,即美国大学本科的计算机学生所受的数学教育原本就是不够的,完全不配作为computer science应有的数学教育。而后他立刻又说,“正因你的基础不够,我们才要同时去努力,你努力把基础补好,我努力让授课的内容能被你听懂”…对于analytical thinking和终身学习,他警告我们不能满足于所谓的pattern matching,依靠记下的公式去解决已知的题目,而是要真正学会analytical thinking,才能有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教授说大脑就像肌肉,只有不断去重复锻炼才会变得强大。随后他以自己举例,”there is a saying in English, you cannot teach old dog new tricks, well, I’m an old dog, but I’m always learning”…结合他75岁高龄仍对各种文献甚至作者的人名信手拈来,并仍然活跃于计算机学界的一线发表着论文,其终身学习的当头棒喝令我无地自容…我与我的同学聆听了教授长达一小时的独家教诲,而后我们二人一致认为这一个小时所学远超硕士生涯以来所有课程。也是那一天起,我心中突然动了不知死活的申博的念想。
我在那之后去图书馆借到了一些书,尝试弥补自己脑海中缺失的代数常识。如是做了几周,也逐渐找回一些对数学这个已然疏远的学科的热情。我相信没有人不痴迷于解出难题的快意,只不过出于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差异,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以一个足够高的频率去享受这样的快感。同时,当我肆意地在UIUC工院图书馆与主图间遨游时,也猛然意识到流连于象牙塔间的日子已然进入倒计时,或许硕士毕业之后我便再无机会接触这样海量的纸质书籍和线上畅行无阻的论文资源,我终究是即将结束自己厌恶了十几年的学生生涯。每当我想到此,都不免怅然若失,不知今后有谁会来阅读此文,假如你读到此处,愿君珍惜自己沉浮于学海的光阴。
一些决定
近日,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缘由,我武断做出了申请博士的决定。我向不少身边的人讲诉了这个决定,并且出于一些原因我不能半途而废。
我自知这个决定极端荒唐,其做出的时间和我自身的实力都在狠狠地敲打并嘲讽着我。我不愿在此做过多的解释,上学期教授的一席话可以被视为我妄想申博的主要动力。即便我的理智不断地提醒着我此时的荒谬,事已至此,我想我还是不如选择坚持。说来可笑,自大四起我似乎对外对内都不断诉说着自己的胸无大志,甘愿平凡去过快乐的一生,然而我心知肚明,嘴上说是认清现实放弃年少轻狂的理想,心中不过是不想亲眼目睹理想最终破灭的那一瞬罢了。
无论如何,这次只能硬着头皮去见证那一瞬了。
一些改变
虽说于学术成就而言,我的大学生涯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但乐观地讲,还是在别的方面有些许值得庆幸的改观:
- 相较高中而言,我在人际关系上,“风评”似乎变好了一些,这或许与我给陌生人留下的错误印象不无关系罢。
- 在大一时期我开始练习长跑,其起因自然是受《强风吹拂》的感染,以及我对自己没有长跑天赋感到十分不悦。坦白说,长跑似乎是我唯一没有天赋的运动。后来几年我出于各种原因,断断续续进行着长跑的训练,到研究生时期已然开始接触半马这样的长距离,算是能体验到压榨自己极限的快感。
- 在本科时期一度想尝试街健,虽然终究没能解锁任何一项神技,但相较高中时只会打打篮球的我,身材和身体素质都有不小的改观。
- 我开始重拾一些儿时的爱好,例如国际象棋与绘画。纯粹是沉迷于在这两样事物上不用花过多力气就可以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果的些许优越感,以此弥补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失败感。当然,国际象棋给我带来的还有很多的社交机会,以及我偶尔会通过连续的高强度对弈判断现阶段自己大脑是否在线。
- 我掌握了一点制作食物的常识,做到了可以不让自己饿死,同时也认清了自己没有烹饪天赋的现实。
- 我对“朋友”的亲疏程度有了更好的把控,我不再如高中那样将所有的朋友一视同仁,而是让他们所有人自最疏远的起点开始,逐渐向更深的层级发展直至某个“止步于此”的瞬间。这听起来或许很幼稚,但它确实替我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交,以及交往了更深远的朋友。
- 由于助教的工作,我已经可以做到状态自然地在一整个教室的学生面前以英文授课(不论人数多少,只要只有学生就行),这在我本科的前几年时看来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 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出于一些原因我开始尝试欣赏艺术,例如阅读一些文学作品,看一些影视作品,虽然不至于有质的飞跃,但确实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
- 我对日漫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观,在大学前我非常不理解所谓“二次元”,而如今我不断在各种日漫作品中看到了别处看不到的精神寄托。我在动漫中看到了跑者对更强而非更快的追求,武士拔刀即是赴死的觉悟,对一些没有来由的恶的探讨,以及对一些青春恋爱美好的歌颂。最重要的一点是,我逐渐用刃牙中“纯度不够”的评价来解释所有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因为细想所有未能完成的目标,似乎都可以归因于自己的纯度不够。而我所追求的“纯度”,似乎又好像只能存在于虚构的动漫作品当中。计算机领域的不少牛人都是“高纯度”的二次元,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出于类似的动机。
一些不变
不变的东西太多了,列举不完。不过最近最显著的一项便是我仍然放不下对一些古老技术的执念,即相较于火爆的AI领域,我更愿意花精力于一些即将过时的科研领域。其主要原因是我无法完全理解人工智能背后的一些数学逻辑,同时我也无法说服自己去研究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
有许多朋友劝说我认清现实,尽早投身AI的浪潮。然而即便我能意识到那样的选择是合理的最优解,内心却还是不愿放弃自己最后的一点执念。或许明年的此时,我已迫于生计彻底洗心革面追随时代的浪潮,但趁着我最后一点在象牙塔内仰望星空的时光,我还是愿意多看点以后没机会看到的风景。
一些动机
写这篇博客花掉了我一整个下午和夜晚,但愿它的作用对得起它占用的时间。这篇博客的动机在于近日一些事情令我不得不做出的反思,我惊恐地发现一些身边的朋友对我在各方面的能力有不同程度错误的认知,我平日对不熟同学的谨慎态度竟被错认为一种心智的理性和术业能力的高级感,这令我受宠若惊的同时又隐隐不安。诚然,我察觉到一些与我不熟的人出于一些对我表象的误解而愿意与我结识,在对我的了解逐渐加深后,他们有的一笑了之,成为我亲密无间的朋友,有的失望离去,留下我不小的遗憾。我实在不愿意他人满心希望而来,看到的却是面具下碌碌无为的我。既然如此,我便想尽量让自己向营造的表象靠近一些,以免往后更多的误解。
此外,我一贯非常依赖与朋友的交流,然而最近的现实因素令我时常苦恼于无人诉说内心的情感。所幸不是真的失败到没有朋友愿意倾听,而是我深知人的悲欢并不相通,而愿意听我倾诉的对象终究不能共情我的所有感受。于是我决定借此机会将这些想法记录,也作为人生的一个checkpoint。我不指望有读者能与我共鸣,只是通过此文发泄一下自己表达的欲望。
我一直记得高中时语文老师用于激励我们的话,
剑未佩妥,出门已是江湖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我时常这样安慰自己,哪怕一事无成,我至少还没丢掉那颗少年的心吧。
2025年6月28日
美国 伊利诺伊州 香槟